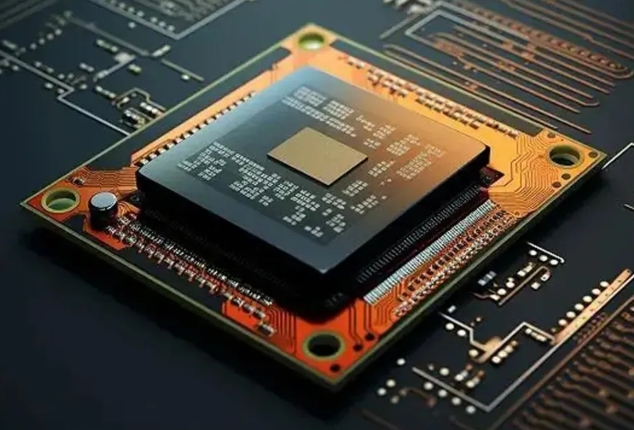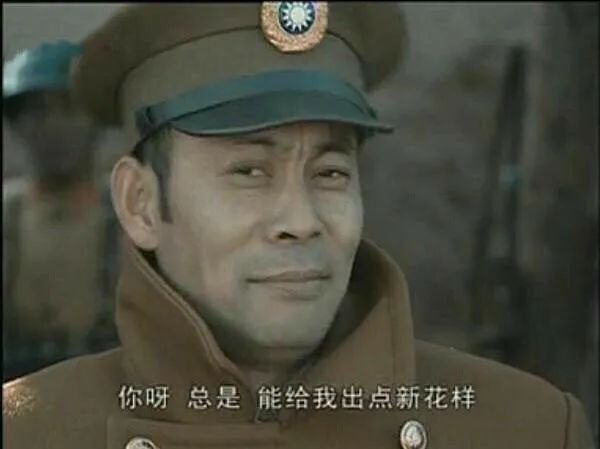赞
赞
01
前两天我写了一篇看看半年报,里面除了回顾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意以外,还简单提到了上周开的最重磅的会议:中央城市工作会议
在这个会议中,明确了两个转向和五个转变
这两个“转”意味着,过去30年的狂飙突进的“中国城市化”阶段,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
用一个大家更容易理解的比喻来形容,过去这四十多年的快速城市化,就像一场世界杯比赛。
四十年前,中国城市之间进行的是“资格赛”,谁都有机会,谁都有可能在300多个地级市中发展起来。
二十年前,中国城市之间进行的是“小组赛”,谁都有有机会在小组中脱颖而出,以一二名进入决赛圈。
那么今天,中国城市之间进行的就是“淘汰赛”,比的已经不是谁能脱颖而出,而是谁不在新时代掉队。
02
前几天,隔壁子明同学写了一篇,未来十年的新经济周期,里面也提到了这次“中央城市工作会议”。
文章中说:
每一轮的城市工作会议,都是要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换引擎。
每次换引擎,都需要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:一个是钱(资本、技术)从哪里来,一个是人(劳动力、资源)从哪里来。
…………
为了避免“大干快上”搞出来大量的重复建设,这一轮产业升级只会聚焦于少数城市,但少数城市的消费群体数量不足(不是消费力不足),最终就一定会形成AI城市消费群的概念
那么,哪些城市在这一轮中有机会呢?大多数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呢?
这也是我最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。
刚好,前几天在这个“中央城市工作会议”召开之前,我“心有所感”写了一篇:“未来”的十二座城,你在么?
(真的是心有所感哈……)
文章里面提到了我心目中的十二座城市,分别是
北京,上海,重庆,深圳
广州,成都,杭州,武汉
南京,长沙,郑州,西安
03
这个名单出来之后,争议蛮多的。
这里解释下,这个名单可以理解为我所期待到2035年,能够“产业升级成功”(AI),在这一场“城市淘汰赛”中跑出来的十二名。不意味着今天就得出了最后的结果。
不过我们今天可以扩容一下,把有“资格”参加“决赛圈”比赛的城市,都列一下,给到大家更多选择,大概有30个,分别是:
北京 上海 深圳 重庆 广州
苏州 成都 杭州 武汉 南京
宁波 天津 青岛 无锡 长沙
郑州 福州 济南 合肥 佛山
西安 东莞 温州 昆明 南昌
贵阳 哈尔滨 石家庄 长春 太原
整体下来能有资格,有可能,在决赛圈“活”下来的,大概也就只有这些城市了。而其他城市,大概就是子明同学提到的“AI城市消费群”概念中的“消费群”了。
04
中国城市格局的深刻转向——从遍地开花的“小组赛”进入残酷的“淘汰赛”,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——对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普通人而言,影响都将是深远而直接的。
在这场城市版图的重新洗牌中,被动等待的结果可能是被“消费群”化。我认为,对于我们大多数人,面对这种趋势性的变化,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积极应对,寻找自身在新时代的坐标。
重新锚定你的“坐标原点”:职业发展与城市选择必须高度协同。
过去“去城市闯荡总有口饭吃”的普适经验正在失效。未来,产业升级引擎将高度集中在入选“决赛圈”。
这意味着高附加值、面向未来的新经济岗位(如AI、先进制造、研发、专业服务、新消费业态的核心环节)将加速向这些城市汇聚。
所以,我们需要深刻审视自己的行业前景是否深度绑定在这些“引擎城市”?
对于年轻人、或有意转换赛道者,选择去这些城市“上岸”发展,将是分享新一轮产业红利的最直接通道。
即使暂居非核心城市,也应优先服务于能链接这些核心城市需求、具有“AI消费群”服务价值的行业。避免将职业根基扎在大概率面临“消费群”化的城市和产业之中。
优化你的“核心资产”:房产与非实物资产需重新配比。
过去“房子就是硬通货”的黄金时代落幕。大规模增量扩张停止,存量提质成为主调。
非核心城市、非核心地段的房产流动性将面临巨大挑战,价值增长和“保值”潜力急剧收缩。
所以建议,收缩绝大多数城市房产配置的权重与范围。 居住需求应聚焦于“决赛圈”城市、尤其是其核心功能区域(科技城、核心CBD、成熟优质学区或生态宜居区)。
投资性房产需极度谨慎,若非十二城级别的顶级优质标的,应优先考虑流动性。
拥抱“流动性”与“在地”结合的新生活方式:资源依赖从“绑定”转为“调用”。
城市“淘汰赛”必然带来资源分配的悬殊。意味着非核心城市的生活品质(如高端医疗、顶级教育、前沿文化体验)在物理空间上将越发依赖核心城市的辐射。
所以我们不妨灵活布局,双重身份。 将家庭生活的“大本营”选择更倾向于成本可控、环境宜居之地(可能包含部分“决赛圈”城市,也可能依托其辐射圈),不再单纯追求物理空间上“面面俱到”的资源堆叠。
同时,保持对核心城市圈(尤其是十二城)关键资源的链接与“调用”能力—— 这包括获取其溢出信息、通过网络合作承接其项目、利用其远程服务能力解决核心需求、甚至具备短居其地享受顶级资源的能力。
05
当然上面这些建议还是更多的侧重于国内视角。
这样一个变革的大时代,所有的“有志青年”,或许还应该有全球的视野,不管是纽约,东京,还是伦敦,巴黎,又或者是新加坡,首尔也都是一个可能的选项。
“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;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;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: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。”
1998年《新华字典》的这个关于“前途”例句,并不是许多人口中的笑话。而是那个时代真实的感受,因为不管是哪一个,都意味着他们拿到了“城市”户口,跳出了“农门”,和中国80%当时的同龄人相比,他们当然都有“光明的前途”。
无独有偶,1998年修订版《新华字典》中关于“城市”一词的例句是:
“城市逐渐在增加。
或许,如果下次《新华字典》再次修订,例句或许会变成:
“不少城市,正逐步消亡……”
 赞
赞
 赞
赞